如今,資本的供應鏈正被三種現象扭曲。前兩種是投機泡沫,它們可能像過去400年中屢見不鮮的先例一樣,從金融領域蔓延至實體經濟。第三種則是來自國家層面的空前沖擊,正在我們本已復雜的政經體系中強行確立前所未有的主導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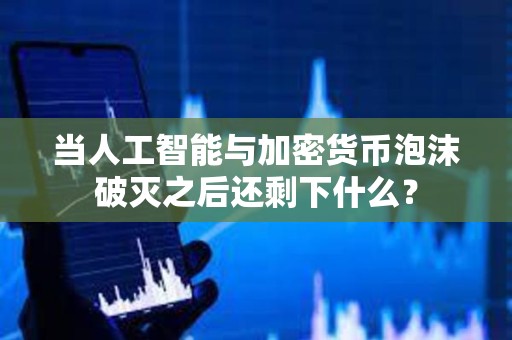
先說泡沫。當前金融市場——無論是公開市場還是私募市場——正顯現出兩場并行的投機狂熱:一場圍繞加密貨幣資產,另一場則聚焦于人工智能相關企業的股票。
加密貨幣市場本質上就是泡沫。它缺乏任何根本性的價值支撐。持有者無法從中獲得現金流;其當前價值完全依賴于“未來能以更高價格賣出”的預期。這與17世紀30年代荷蘭的“郁金香狂熱”如出一轍——當時的投機對象同樣毫無內在價值。
人工智能的炒作周期則屬于更常見的泡沫類型。又一項創新技術橫空出世,其長期經濟影響尚不可知。盡管本月OpenAI推出的GPT-5模型反響平平,可能標志著泡沫已見頂,但最終答案仍需時間揭曉。
兩大泡沫的共同特征是:投資者愿意為那些流動性極低、且毫無治理權的證券支付極高的溢價。從散戶到機構,資金正以前所未有的規模涌入高度投機的非流動性資產。這兩個泡沫最初都源于一個異常的金融環境:實際利率為負,無風險資產的實際回報也為負。一旦膨脹開始,投資者“害怕錯過”(FOMO)的心理便驅動了所有熟悉的泡沫動力學。
金融泡沫的第一定律是:你很容易知道自己身處泡沫之中,卻極難判斷它何時會破裂。然而,研究者已識別出三個預示泡沫終結的信號:
1.需求曲線倒掛:價格越高,需求反而越大。哥倫比亞大學的何塞·謝因克曼(José Scheinkman)與國際清算銀行的沈聯濤(Hyun Song Shin)曾指出,這一現象在1990年代末的互聯網/“.com”泡沫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前均曾出現。
2.新供給涌現:價格的指數級上漲吸引大量新參與者涌入。即便在數字世界,創造一項新資產所需時間也遠長于價格變動速度。加密貨幣價格瞬時波動,而私人股權市場反應迅速,但構建一個新大型語言模型(LLM)卻需要漫長周期。
3.業余投資者主導需求:在泡沫末期,需求越來越多地來自缺乏信息的散戶投資者。
目前,加密與AI市場似乎這三個信號均已亮起紅燈。但兩者破滅的催化劑可能截然不同。
加密貨幣的價格完全依賴需求,而需求來自現有持有者的增持和新買家的入場。當前需求激增,與特朗普政府激進的去監管議程密不可分——這一議程與政府前所未有的腐敗(如發行總統迷因幣等)難以分割。因此,加密貨幣的持續繁榮,似乎取決于特朗普及其核心圈能否維持政治權力。考慮到加密行業在游說和競選資金上的巨額投入,這種政治支撐很可能至少持續到2026年中期選舉,甚至更久。
人工智能泡沫則不同。遲早,當前的高估值需要基本面支撐——即從對計算基礎設施(數據中心等)的巨額投資中產生正向現金流。與加密貨幣(以及400年前的郁金香球莖)不同,押注AI的人需要一個經濟上可持續的商業模式。
誠然,一些企業和創業者已找到大型語言模型具有經濟價值且商業可行的應用。但要使當前AI估值勉強站得住腳,必須滿足兩個條件:第一,AI應用的市場規模足以產生與巨額投資相匹配的現金流;第二,同樣重要的是,其經濟模式必須能實現穩定均衡,讓競爭性供應商均能獲得正向現金流。
第二個條件可能難以實現。由于提供AI服務的固定成本遠高于每單位服務的邊際成本,其經濟模型令人望而生畏。一旦價格趨向邊際成本,所有參與者都將虧損。這正是為何以往的技術革命往往最終演變為穩定的寡頭壟斷(難以維持)或受監管的壟斷。
鐵路、電氣化和互聯網的歷史均與此相關。每一項技術在發現可行且可擴展的應用之前,都需巨額投資于物理基礎設施。如今,我們視這些產業為理所當然,卻忘了它們的發展歷程充滿連續破產,以及各種國家干預以保護競爭者免于自毀。正如常發生的那樣,個體對激勵的理性反應,卻導致了極具破壞性的協調失敗。而貫穿始終的是,巨額投機資本在一次次金融危機的間歇中,資助了這些變革性網絡的建設。
對于AI而言,分析師尼古拉斯·科林(Nicolas Colin)所稱的“算力-能源棧”(compute-energy stack),正是前兩個世紀的鐵路軌道、發電廠與電網、光纖電纜與服務器農場的現代等價物。資本再次必須首先流入那些經濟價值尚不可知的資產。若AI泡沫能在不引發劇烈斷裂的情況下,帶來長期、穩定且盈利的成果,這在資本主義歷史上將是前所未有的。
20世紀,為前沿科技提供資本的供應鏈經歷了制度性變革。在1980年代之前,由大型技術壟斷企業(杜邦、AT&T、通用電氣、IBM、施樂)的壟斷利潤資助的工業研究實驗室,在美國創新體系中扮演了關鍵角色。但1982年,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裁定股票回購不構成“市場操縱”,為壟斷租金開辟了替代用途。自此,這種現金使用方式不斷增長。2024年,美國上市公司股票回購總額達9425億美元,比企業研發投入總額高出50%以上。
當然,到1980年代,聯邦政府為贏得二戰、冷戰以及發起“抗癌戰爭”而動員科學的體系已趨成熟,部分抵消了舊科技壟斷企業的退出。但這引出了第三個、也是最具破壞性的進展:特朗普政府對美國科研事業前所未有的打擊。
重返白宮后,特朗普立即對國家衛生研究院(NIH)、國家科學基金會(NSF)、能源部高級研究計劃署(ARPA-E)以及環保署研發辦公室等戰略資助機構下手。更糟的是,他正對長期以來孕育科學發現與技術突破、支撐美國競爭力的研究型大學發動正面攻擊。這些機構正被系統性地削弱。
這一破壞計劃由管理與預算辦公室主任羅素·沃特(Russell Vought)主導,并在極右翼傳統基金會臭名昭著的《2025年項目》(Project 2025)中公開預演(沃特本人參與撰寫)。表面目標是清除多樣性、公平與包容(DEI)項目及一切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深層使命則是瓦解“新政”遺產,將美國帶回1920年代的政經模式。唯有國防部將基本不受影響。
雖然無法量化這一計劃的長期后果,但其對美國經濟乃至全人類的負面影響幾乎毋庸置疑。美國創新經濟曾帶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物質進步;如今,它正被系統性地致殘。
加密與AI泡沫不僅早于這場沖擊而出現,它們的興起也很大程度上脫離了哈佛商學院保羅·戈姆珀斯(Paul Gompers)與喬希·勒納(Josh Lerner)在其行業經典著作中所記錄的傳統風投周期。盡管存在一些風投支持的加密項目(如Coinbase),也有像安德森·霍洛維茨(Andreessen Horowitz)這樣的風投機構積極成為加密倡導者,但大部分資金仍來自散戶投資者。
如今,得益于去監管化帶來的機構支持潛力,散戶對加密的投機重獲生機。若無強有力的國家支持,人們本應早已看清:這種投機已達到任何龐氏騙局自我毀滅的極限。看看“加密金庫”公司模式的泛濫吧——該模式由MicroStrategy(近期更名為Strategy)首創。其狂熱的創始人兼執行主席邁克爾·賽勒(Michael Saylor)似乎創造了一臺永動機:不斷基于其比特幣持倉價值數倍的公開市場估值融資,用以購買更多比特幣。數十家追隨者紛紛效仿,但許多公司股價已低于其加密資產價值,Strategy的股價在8月下跌了15%。換言之,它們已觸發了上述第二個信號(價格膨脹催生新供給)。
相比之下,支撐AI泡沫的真實資產資金主要來自大型科技平臺公司。一些風投試圖參與AI熱潮,即使這意味著放棄估值與治理的風投原則。2025年上半年,OpenAI從軟銀等“著名泡沫投資者”牽頭的混合來源中籌集了高達400億美元。第二季度,五筆類風投交易為AI相關公司融資超10億美元。
在風投業內,連續四年退出與分配(實現利潤并分配給投資者)極少,行業本身已兩極分化:一派堅持傳承使命,控制規模,深度參與早期項目的治理;另一派則轉型為私募股權規模的資產聚集者與費用收取者。對整個行業而言,對AI的日益聚焦已耗盡了2021年“獨角獸時代”所募集基金的“干火藥”(dry powder)。
盡管更廣泛的金融環境已從2021年前非常規貨幣政策催生的過度投機狀態中正常化,但風投的未來架構仍不確定。問題不僅在于加密與AI泡沫仍需自行出清。更根本的是,該行業再也無法依賴美國政府精心策劃的創新供應鏈。如今,這條供應鏈的許多環節正被特朗普政府削弱或斬斷。
風投模式誕生于美國,但其未來或許將屬于中國與歐洲。隨著基于科學的變革性技術之流枯竭,它在其本土長期扮演的戰略角色將日漸式微。這條供應鏈歷經三代人建成,重建之路將無比艱難。
<strike id="ykeqq"></strike>
<fieldset id="ykeqq"></fieldset>